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
我以为先生的业绩,留在革命史上的,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回忆三十余年之前,木板的《訄书》已经出版了,我读不断,当然也看不懂,恐怕那时的青年,这样的多得很。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,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,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序,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。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,正办杂志《浙江潮》,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,却并不难懂。这使我感动,也至今并没有忘记,现在抄两首在下面:
前一些时,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,赴会者不满百人,遂在寂寞中闭幕,于是有人慨叹,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,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。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。官绅*,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;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,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,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,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,和时代隔绝了。纪念者自然有人,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。

章太炎走出门,看到马车已在门外等待。他坐上马车后,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一处大宅院。主人对章太炎盛情款待,还有很多陪客。陪客中有印度人、欧洲人和*。而*则是三国时期曹魏玄学家夏侯玄,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。
章太炎心怀仁慈,号召几位判官一起废除*,以免地狱众生继续受苦。之后,他就开始在地府担任判官一职。但章太炎所判的案件并不复杂,也无重大案件,基本都是械斗谋杀、*钱财之类的事。如此连续工作了20多天后,章太炎开始心生厌倦。
他想了一个办法,写了一张请假条,然后在家中烧掉。当天晚上,果然没有马车来接他到冥府断案。但到了第二天,这个办法就不灵了。章太炎不胜其扰,便向好友宗仰和尚求助。宗仰和尚给了章太炎解决办法,他静心打坐了三月之久,便不再梦到去冥府断案之事。后来章太炎回想他看不到冥府施刑的过程,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是生人,又没有那么大的业力,所以才会看不见。
章太炎最狂的一句话
但关于冥府判案一事,章太炎并未公开宣讲,而是与关系密切的友人进行了分享。直到他去世后,他的信件被女婿发现,才将此事公之于众。而除了章太炎外,中国历史学家,民国政要黎澍也曾在19岁那年被接到冥府担任判官一职,他还专门写了一本《幽冥问答录》来记录此事。当然,这些内容究竟是他们亲眼所见,还是编造出来的,还有待验证。大家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!
据王鏊介绍,梅尧臣是总审判长,他们两人加上其余六人,是审判官。9人一起分主五大洲的刑事案件。而章太炎和王鏊,则负责东亚的刑事案件。
这就可以解释太炎先生晚年指挥*所编《同门录》里,为何出现明显的纰漏。据说吴承仕曾当面问过太炎先生,为何《同门录》里没有鲁迅、许寿裳、任鸿隽等人名字,去取是否有意。太炎先生的回答很妙:“绝无,但凭记忆所及耳。”即便我们相信太炎先生的解释,可如此郑重其事编纂《同门录》,居然会遗忘其时已大名鼎鼎的鲁迅等人,起码可以说明在章太炎心中,怎样才算是真正的“入室*”。
就在听章太炎讲学的同时,周氏兄弟开始了其以医治国民*为目标的文艺事业。若如是,鲁迅、周作人对于《说文》等传统学问的态度,与从大成中学转来的钱玄同等,必定会有很大差异。不管当初是否只从“了解故训,以期用字妥帖”来修习《说文》,其中途退场,以及日后的不以治经、治史、治子为业,都决定了太炎先生之不以此等学生为傲(政治立场当然也是一个问题)。
尽管在后世学者看来,鲁迅的*世界与思维方式,受章太炎影响很深,可从专业著述角度考虑,鲁迅确实算不上章太炎的“得意门生”。不过,《域外小说集》封面,依稀可见此课程的影响:在长方形希腊图案的下面,篆书题写书名,均依《说文解字》。还有,鲁迅晚年曾再三表示,准备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。
鲁迅和章太炎立场一样吗
太炎先生的医学,不是纯粹从传统医学着手的,他还十分注意从西学中汲取营养。太炎先生在研究中西学理基础上,写成了《菌説》、《原人》、《原变》等文章。他融会中西,更造新医,对我国近代*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章太炎因为看过几大箱*书,写过些医学著作,便自认为医术高明,所以很爱替人医病,他不仅为亲属或友邻开过药方,还曾为革命家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过药方。
章太炎就是这样一个儒侠,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,一生特立独行,也卓尔不群。一生七次被捕,三次坐牢,革命不忘治学,治学必须革命,可见风骨,他的国学修养和士人*给辛亥革命带来了巨大影响。
著名国医惲铁樵先生説:“太炎先生为当代国学大师,稍知治学者,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,医学乃其餘绪,而深造如此,洵奇人也”。也有人称其为“国医革新之导师”,确实如此。
他骂慈禧“每逢万寿祝疆无!”,骂光绪皇帝:“载湉小丑,不辨菽麦”,骂康有为: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。鲁迅还在一篇文章中说:“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*,好发议论,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。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,曰‘章疯子’。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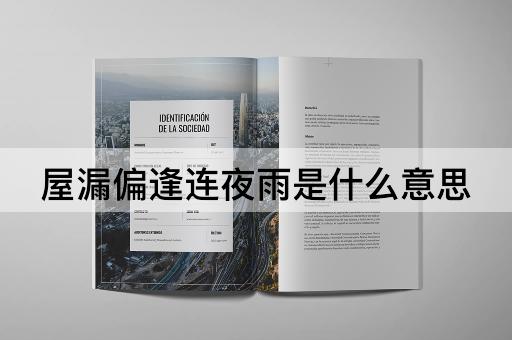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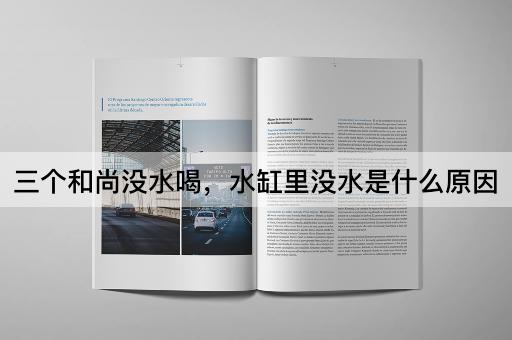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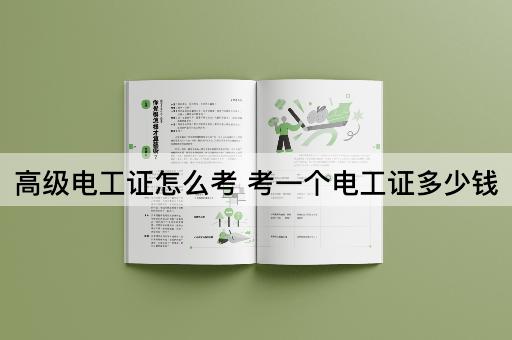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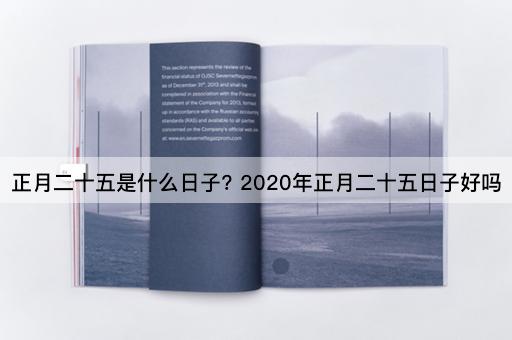
添加新评论